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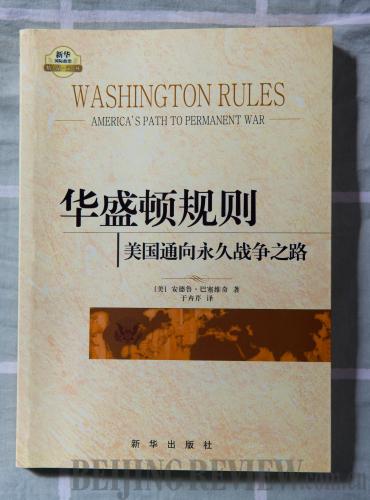
波士顿大学的安德鲁•巴塞维奇教授近些年由于连续写了多本尖锐批判美国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的书,已经成为美国一位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CNN在介绍他的新著《华盛顿规则:美国通往永久战争的道路》时,赞扬他是反战人士中的“主导声音”。但对中国公众来说,在新华出版社年初出版此书的中文版以前,他的名字还是颇为陌生的。
在巴塞维奇教授看来,美国过去六十年的国家安全政策可以用“华盛顿规则”来概括。它代表一种共识(亦称“华盛顿共识”),其中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所谓的“美国信条”,它“要求美国——只有美国自己——领导、拯救、解放并最终改变世界。”一是所谓的“神圣的三位一体”,它“要求美国保持全球的军事存在,配置兵力进行全球力量投射,依靠全球干涉主义政策打击现存或预期的威胁。”这两部分相辅相成,构成“华盛顿规则”,“信条”讲的是目的,“三位一体”讲的是实践。
作者在分析“华盛顿规则”的形成过程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人对军事力量和军事机构基本上持怀疑态度,如果不是完全敌对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初,这个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军事力量的喜爱成为美国性格的核心。”作者着重说明了美国出版界巨头亨利•卢斯在促成这一转变中的重要作用。他在1941年发表于《生活》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美国世纪”这一概念,鼓吹二十世纪是美国肯定要领导全球的时代。他这篇带有纲领性的言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华盛顿尤其得到强烈的响应。
在“神圣的三位一体”的缔造者中,有两个人物显得特别突出。一个是1951-1961年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另一个是在1948-1957年掌管过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四星上将柯蒂斯•李梅。这两个机构行使了超出自身职权范围的权力。中情局遍布于全球的工作站,除了从事通常的间谍活动以外,还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散布虚假信息、贿赂、破坏、暗杀去影响其它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李梅则很快把空军战略司令部改造成了一个随时能投入战斗并能多次毁灭不仅是苏联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全球核打击力量。
美国的历届总统,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喜欢标榜与竞争对手或前任不同的政策,但没有一个人背离过华盛顿规则。作者指出,“对美国的全球军事存在、力量投射和干涉主义提出怀疑——正像让•保罗和丹尼斯•库斯尼奇在1988年总统初选时所做的那样——就是表明你自己是个不正常的怪人,要么是信息闭塞,要么是不太可靠,当然也不是一个适合担任国家要职的人”。
让•保罗是共和党议员,他主张有限权力的宪政政府,一贯反对美国的对外军事干涉。丹尼斯•库斯尼奇是民主党议员,他反对将武力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这两位议员属于为数很少的反对当前美国军事干涉利比亚的政治家,他们公开质疑这项行动违反宪法。
同样,美国推行“华盛顿规则”在民众中也很少遇到反抗,越南战争是唯一的例外。但在战争结束后仅仅十几年的时间里,因在越南遭到失败而根基严重动摇的华盛顿规则已经完全得以恢复。作者分析说,这首先得益于找到了替罪羊——把失败归罪于自由主义者、学者和所谓有偏见的媒体。其次是物色适当人选来推翻越南战争经验已经作出的明显结论。其成果是1976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持策划的《越南的遗产:战争、美国社会及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一书。这个有很大影响力的委员会集研究所、思想库和出版社于一身,为讨论世界问题和美国及其它国家面临的外交政策选择提供论坛。这部书的二十四位撰稿人全是白人,男性,除两名外全是美国人。其中有著名政治家,过去和未来的高官,著名的学者和报人。他们都是社会名流,会把不同意见限制在那些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事情上,而不会有人站出来挑战“华盛顿规则”。
苏联的解体和欧洲的统一照理应使“神圣的三位一体”因过时而不再必要。但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存在,包括在欧洲、日本和其它地方的驻军和频繁的军事行动,仍然没有多少变化。作者写道,“所以,五角大楼设计了一个新的理由….需要美国在海外的驻军来促进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诞生。”
“9•11”事件后,布什宣布向恐怖主义开战,提出了“预防性战争”的主张。总统拥有基本上不受限制的权力。他和他的顾问们所认为任何“保持美国安全”所需要的行为都是合法的。据作者观察,在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华盛顿更倾向于把武力作为首选工具。
作者列举的事实和数字表明,遵循“华盛顿规则”,除了夺走无数美国人的生命外,还使美国债台高筑。半个世纪以前,美国还是一个债权国,但现在已变成一个债务国。在小布什当政的八年期间,国债几乎增加了一倍,达到10.6万亿美元。据官方估计,到2019年,这个数字将达21万亿,大大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华盛顿规则”和美国公民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讨论可能是本书最深刻、最有意思的部分。作者指出,“华盛顿规则”之所以能经久不衰,原因之一是它顺应并强化了美国公民文化的某些“成问题”的方面。巴塞维奇指出,当今美国的公民概念仅仅“要求你交你该交的税,再就是不要公然违反法律”。他用“贫弱”二字来形容这个公民概念,批评它“把个人选择置于集体责任之上,把一时之欲的满足置于长期福祉之上”。
作者用两个例子来说明美国的当权者在推行“华盛顿规则”时如何利用了这个弱点。一是在越南战争后期的1973年改义务兵制为志愿兵制。表面上看是给予公民一种类似自主权的东西,许多美国人也把它理解为自由。实际后果是进一步削弱了公民的责任意识和对美国海外军事行动的关心和监督。二是用大举国债的办法来支付海外军事开支,把债务责任推到未来美国人的头上,从而避免了因过度征税而引起人民对海外军事干涉的强烈反对。因此,作者认为,“华盛顿规则”之所以能通行无阻,普通的美国人也难辞其咎。
作者在书中呼吁回归到美国的建国理念,以取代华盛顿规则。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他著名的1796年离职告别演说中,敦促他的国民制定一条独立的路线,使美国能够“给世界树立一个崇高而独特的榜样,它的人民总是被高尚的正义和仁爱之心所指引”。他激励国人立足本土,不要站在外国的土地上。二十五年后,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他后来成为第六任美国总统)在一次众议院的演说中进一步阐述了华盛顿的主张。他说:美国“衷心希望所有国家自由独立。她只捍卫自己,她只当自己的辩护士”。他警告“不要到国外去寻找怪兽来射杀”,“不要在他人的旗帜下当兵”,以免使自己卷入各种肮脏的战争。
巴塞维奇旁征博引,用一种基于事实和具有说服力的方法来说明自己的论点。谈的是他自己国家的问题,但有时他看问题的方法似乎多少受东方哲学的影响。他使用“阴和阳”来概括杜勒斯的中情局和李梅的战略司令部既互为竞争对手又互相依存的关系。书中有几段话讨论了作者假想的一个中国海外扩军计划 ——这个计划看起来很吓人,但在现实的美国全球军事态势面前仍大为逊色。这几段话可以解释为作者向华盛顿人士提出的一个委婉建议,让他们能换位思考。显然,巴塞维奇很理解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名言的哲学智慧。
巴塞维奇提出的这个假想是,中国国防部长有一天宣布了这样一个计划(下面只是一个简略本):
增加军事投入,使解放军每年的花费最终超过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德国、法国和英国国防预算的总和;在全世界各个战略敏感地区,包括拉美,设立为数众多的“前沿解放军守备部队驻地”;就入境及飞越领空权问题同一些国家进行谈判,目的是便于人道主义干涉和促进全球稳定;把全球划分为几个涵盖广袤领土的军事区域,设立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非洲、中东……包括北美等几个司令部,另加一个中国太空司令部,分别由一位中国四星将军负责;等等,等等。
作者写道,中国国防部长无疑会提醒其它国家不要把这个计划看作是对它们的威胁,中国真诚致力于与其它国家和平共处……中国这个有悠久文明的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国家定会对世界稳定作出贡献。
作者断定,不管是美国或其它任何地方的观察家都不会因这种保证而感到宽慰。
巴塞维奇教授的独特背景增加了这部书的可信度。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在美国军队中服役二十三年,其中有两年参加过越南战争。他退伍时是上校军衔。此后他转向学术研究,在普林斯顿大学专攻美国外交史,获博士学位。在去波士顿大学任教以前曾在西点军校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书。
在本书的序言中,作者称自己是“一个迟钝的学生”。他叙述说,作为一个年轻人,他乐于接受正统思想,习惯于服从权威。直到中年,他发现过去接受和相信的东西常常与现实相悖,这时他的真正教育才开始。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与世人分享他的经验。
没有一本书是完美无缺的,巴塞维奇的这部书也不例外。缺乏从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讨论问题,似乎是一个明显的缺陷。新华出版社在原书问世后不到六个月就推出了中文版,肯定是一项成就。但译文未能始终忠实于原文,即使是不细心的读者也能发现一些差错。
尽管如此,许多中国人会满怀兴致读这本书。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愿意和美国大众一起,向被《纽约时报》书评赞扬为“热烈而精明的和平贩子”的巴塞维奇教授致敬。因为他的这部书不仅提供了一个简明而深刻的对美国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的历史回顾,而且书中的很多论述发人深省。例如,他批评当今的 美国人在培养品德方面缺乏兴趣,而狂热追求经常是用财富、名气来定义的幸福。当作者讲这话时,他正好指出了当前许多社会的通病,其中也包括中国社会。他关于“华盛顿规则”起源于卢斯的“美国世纪”的论述,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有些国人热衷于议论“中国作为大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世纪”,这对于我国的健康发展,恐怕没有多少好处。(作者是《北京周报》前总编辑)